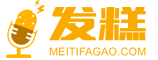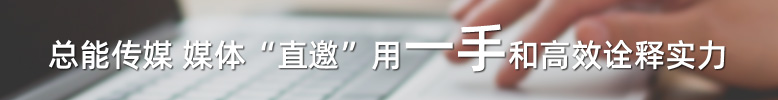数据殖民主义理论与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对话
来源:时间:2022-09-06热度:0次
No.1
数据殖民主义的缘起与核心内容
文章主要关注英国学者库尔德利与美国学者梅西亚斯提出的理论框架:数据殖民主义 (Data Colonialism)。数据殖民主义与历史殖民主义密切相关,但并非历史殖民主义在新世纪的纯粹延伸, 而是一种基于 21 世纪数字语境的新型殖民主义。在库尔德利和梅西亚斯看来, 数据殖民主义的核心内容包括三点:数据掠夺 (Data Extraction)、 数据关系 (Data Relations)、 数据导向逻辑(Data-driven Bogistics)。
数据掠夺指目前各大数字巨头,如谷歌、脸书等,正肆无忌惮地掠夺个人数据并将个人数据商品化,如同历史殖民主义中的殖民者一般大肆掠夺原住民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而且,这种数据掠夺并非如数字劳工所设想的一般,仅仅对劳动所生产的数据进行掠夺,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无时无刻地收集着个体的各种数据。数据掠夺得以奏效的原因在于社会关系在数字语境下转变为数据关系,这种转换导致个体的社会生活变成了数字巨头可以肆意开采的开放”资源。库尔德利在接受采访时称,数据关系为数据殖民主义所催生的新的资本主义组织的抽象形式与社会关系,这种新型关系为资本对个体数据的掠夺与商品化提供了土壤。在此语境下,社会实践逐渐由数据导向逻辑所驱使,数据导向逻辑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否涉及具体利益,社会成员日益关注社会行为与数据生产的关联,一切以数据为先,这点从目前社会各行业推崇流星为王的现象可见一斑。
所以,数据掠夺、数据关系与数据导向逻辑不仅描绘着数字社会的现状,更昭示着一种数据趋势,这种数据趋势意味着新型的殖民主义土地掠夺。资本不再掠夺物理意义上的土地,而是由人类生命构成的数据领土。那么当数据殖民主义向社会蔓延时,我将面对什么?在库尔德利与梅西亚斯看来,数据殖民主义最终将导致自我(Self)的消解,自我在数据语境下的各种智能机器面前彻底裸露,一切数据皆在数字资本眼前一览无遗,日常生活中无休止的数据追踪与掠夺最终将个体的社会生活变为一无所有的生活(dispossessed life)。这不仅是经济层面上的不平衡,也是精神层面上的间隔,因为,此时的自我显然如同阿甘本所言的Zoe一般,彻底被放逐”。
由上可知,数据殖民主义主要关注数字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入侵,并对此现象进行批判反思。然而,目前关注此现象的研究视角或理论框架并不少,如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工、平台资本主义,等等。数据殖民主义理论究竟与已有理论框架有何差异?或者,数据殖民主义在理论层面上作出了怎样的回应?对此,从库尔德利与梅西亚斯的多篇文献可知,数据殖民主义尝试弥补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工理论对于数据掠夺现象语境的忽视,换言之,该理论框架试图回答为何资本巨头可在数字时代每时每刻地收集个体的众多数据。数据殖民主义无意如数字劳动般将一切数据掠夺溯源为劳动,而是关注到难以用劳动囊括的数据掠夺现象,如可穿戴设备、数字地图使用。因此,数字劳工的剩余价值剥削并非数据殖民主义问题域的核心,个人数据像“开放”的自然资源一般供资本掠夺的常态化与数据的物化(商品化)背后的推动力才是数据殖民主义的讨论焦点。进一步而言,库尔德利与梅西亚斯数次强调,数据殖民主义虽然与传统数字批判理论一般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该理论框架尝试结合历史殖民主义理论,从而实现补充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数字语境下的阐释力。历史殖民主义理论的加入,有利于拓宽传统批判理论的视域,关注到殖民主义如何通过全球资源的掠夺助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以及资本主义又是如何通过规范全球资源将剥削与殖民合理化。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双重批判可有效地揭示数据掠夺不仅是为了商业利润,更是对于人类生命与自由的剥夺。
当然,殖民主义理论的引入也意味着数据殖民主义需要在经验与理论层面上同时回答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何以可能的问题。对此,库尔德利与梅西亚斯主要借鉴秘鲁社会学家奎杰罗的去殖民主义思想,他们给出的答案可简要归结为两点:其一,人们需要意识到生活中的数据掠夺,并且,无论是商业还是治理缘由,一切数据收集的理由都理应时刻警惕,而非简单地接受;其二,有识之士应该效仿不结盟运动,推动数据领域的反权威运动,从而对数字语境下的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形成反动,如库尔德利组织的技术不结盟运动。
No.2
数据殖民主义的经验层面应用
目前已有不少经验研究采取数据殖民主义作为理论框架,讨论的经验对象也颇为多元,如数字平台的电子数据库、跨境生育、数字医疗。然而,在多数经验研究里,数据殖民主义往往被作为某些经验现象的类比,仅仅是在描述哪些经验素材属于数据殖民主义。例如,在数字医疗领域,研究者基于数据殖民主义的“数据关系”数据掠夺”,指出目前数字医疗将病人的数据视为一种资源,并且在悄悄地掠夺这些资源,个体生命在无形中受到数字医疗机构的殖民;在关于数字平台电子数据库的文献里,研究者将脸书的电子数据库类比为殖民时期的档案库,后者在历史殖民主义里主要阻碍被殖民者的知识获取,服务于殖民者的合法性建构,而前者目前正发挥着殖民时期档案库的作用,并不断地通过收集用户数据来实现数据殖民。
这些基于数据殖民主义的研究固然揭示与描绘了当前社会中的各类数据殖民现象,但在此之中,数据殖民主义其实被作为一种隐喻来使用,主要用于现象的类比,相关分析也自然停留在描述层面。这其实与库尔德利与梅西亚斯关于数据殖民主义所作的理论承诺存在矛盾。在相关文献里,库尔德利与梅西亚斯屡次强调数据殖民主义并非一种隐喻,这与目前相关经验研究的理论应用情况显然存在不协调。进一步而言,若数据殖民主义仍然仅仅是作为宏大理论,那么其对于隐喻”的否l不免自相矛盾。对此,不妨借鉴政治学研究者萨托利提出的“概念扩张”来思考此问题。萨托利曾在论述”政治”这个概念时指出,目前“政治”这个概念正日渐囊括四海,无所不包;随着此概念扩张,一切事物都不免落入同一概念的篮子里,但该概念也将日渐抽象与空洞。与此类似,在已有经验研究里,由于缺乏中观层面的阐释,数据殖民主义几乎可对应任何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现象,缺乏边界的界定,数据殖民主义在宏观层面当然可以无边界,但至少在具体经验案例里,一切讨论与分析都应该围绕着有一定边界的数据殖民主义进行,否则这些讨论与分析自然变得无所不包却又无比空洞;在此之中,数据殖民主义本身的宏大理论特性与“隐喻”的边界也将逐渐变得模糊。由此观之,生命与数据转化过程的中观层面阐释缺失无疑成为了数据殖民主义与经验研究相结合时最大的矛盾点,也是数据殖民主义理论本身的理论承诺急需解决的问题。
由此观之,若数据殖民主义要实现理论承诺并为经验研究提供足够指引,关键点在于为生命与数据转化过程的中观层面阐释提供一个切入点,而这个切入点显然需要在“生命”与数据”之间寻找。对此,媒介基础设施(Media Infrastructures)或许可以作为切入点,因为,数据殖民主义所描述的个体生命数据化现象正是以各类媒介基础设施作为前提。在数字技术早已融入日常生活的今日,媒介基础设施遍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数据中心、海底电缆、互联网网关、虚拟路由,等等。它们常常保持着不可见"的状态,但这些不可见的媒介基础设施贯穿数据殖民的每一环节,包括数据生产、数据收集、数据传输与数据分析等。与此同时,以探究数据掠夺常态化为己任的数据殖民主义可提供一个独特的去殖民主义视角(Decolonialism)来观察基础设施与数据的关联,从而拓宽与深化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视域。
此外,库尔德利与梅西亚斯在回应关于数据殖民主义与历史殖民主义关联的质疑时,虽然详细解答了暴力并非二者的关联,二者的关联在于世界观,但其实此回应并未解答数据殖民主义如何继承与发展历史殖民主义。或者说,库尔德利与梅西亚斯的回应只停留在意识层面,主要探讨思想与语境的基础和发展。对此,若借鉴技术哲学视角,作为外置记忆的技术正是解答上述问题的切入点,因为,正是技术让记忆(历史殖民主义)得以在数字时代回忆(重塑为数据殖民主义)。这点其实从一些数据殖民主义的经验研究里也可见一斑,如脸书电子数据库与殖民时期档案库的高度相似。由此观之,鉴于媒介基础设施作为数字时代极其关键的技术物,要真正理解数据殖民主义与历史殖民主义的关联,学界显然有必要从媒介基础设施的角度去关注二者。媒介基础设施研究(Studie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s)或可与数据殖民主义在此形成互补,后文将进一步详细论述二者如何形成中观层面的互补与融合。
No.3
分类与框架:数字殖民主义与媒介基础设施研究
事实上,数据殖民主义的相关文献不乏媒介基础设施的讨论,然而,这些讨论存在两点问题:分类混乱与缺乏系统。分类混乱主要体现在相关研究者对于哪些技术物(数码物)属于媒介基础设施并没有统一分类体系,作为指代的“媒介基础设施”存在繁多的所指。例如,在库尔德利与梅西亚斯的数据殖民主义文献内,脸书、谷歌、海底电缆、数据中心皆曾作为媒介基础设施被指代与讨论,而且这些指代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具体解释,而是自然而然地使用。当然,把上述技术物(数码物)皆理解为媒介基础设施这种分类方式虽然显得大而泛之,但这本身其实也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把它们都放在同一层面看待。例如,在库尔德利与梅西亚斯的论述里,海底电缆与脸书都曾被指涉为基础设施。鉴于海底电缆与脸书都参与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众多数据实践,也都在不显眼之处组织着这些实践,库尔德利与梅西亚斯将二者都视为媒介基础设施不无道理,但把二者视为同一层面的媒介基础设施显然并不合理,因为前者与后者无论在物质形态上,还是各自与人们互动的方式可谓截然不同。分类混乱的问题则导致目前数据殖民主义涉及媒介基础设施的论述往往流于表面的功能描绘,而缺乏系统地探究媒介基础设施与数据殖民主义在各环节的互动。例如,相关论述仅停留在宏观地叙述数据掠夺基于这些媒介基础设施得以实现,或资本正借助它们实现全球数据资源的殖民,而并未系统地关注这些媒介基础设施的物质形态、所涉及的关系网络、人们日常的技术实践如何与数据殖民主义形成勾连。因此,借鉴目前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相关讨论,以及结合数据殖民主义所涉及的各环节,媒介基础设施或可在此分为三类
图片
如表1所示,实体类主要指海底电缆、数据中心等具有明确实体的媒介基础设施,它们往往规模庞大,作为全球数据流动的基底,一般难以改动且形态固定;数码类主要借鉴技术哲学家许煜提出的数码物概念,此类媒介基础设施以元数据、元组数据库、语义网络作为根基组织着全球数据的流动,如IP网关、Cookies。数码类媒介基础设施虽然存在于虚拟数据之中并可以受改写,但其内在的关系网络在变化的同时也保持着稳定的内核。作为数字平台与基础设施的混合体,平台类媒介基础设施与前两类相比属于更“软”的基础设施,如脸书、微博、微信;一方面,由于平台特性,此类媒介基础设施属于最贴近内容与公众的一端,更容易随着公众诉求或资本目的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虽然公众几乎每时每刻关注各大平台上的内容,但平台本身的“可见度”却在不断下降,如同基础设施一般,悄然无声地组织着数据实践。上述分类当然并不完美,甚至谈不上成熟,但或许可暂且帮助我们在不同层面上系统地探讨各类媒介基础设施与数据殖民主义的关联。在此基础上,后文简述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分析维度,并探讨这些分析维度与数据殖民主义在中观层面的结合。
在数字时代,人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借助各类媒介基础设施周而复始地生产、上传、获取数据,但同时,人们甚少关注上述过程里的媒介基础设施如何运作,因为只需轻轻滑动或点击屏幕便可实现这些过程。例如,人们在使用抖音时,无需思索算法、数据中心、电缆等媒介基础设施,只需滑动屏幕便可一边获取他人分享的数据(内容),一边生产与上传自身的用户数据。所以,与前数据时代相比,日益智能的媒介基础设施带来了现代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民众几乎未曾知晓媒介基础设施究竟如何运作,更逞论其背后的劳工剥削、资本斗争、数据滥用,媒介基础设施的“不可见性”正不断催生不平等现象。尽管往日研究多将媒介基础设施作为背景,但媒介基础设施研究正是希望通过将媒介基础设施作为研究对象,让媒介基础设施从不可见转为可见,从而揭示其背后的各种不平等现象。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的,媒介基础设施研究主要从物质形态“与话语建构“维度观察媒介基础设施。物质形态主要指媒介基础设施作为技术物存在的本身并非单一实体,而是一个关联体,由始至终都联系着形色各异的人与物,探讨物质形态意味着我们去考察媒介基础设施本身复杂的关联网络,如其技术历史、技术参数等。话语建构则并非以社会建构主义范式下的软性的主观建构为前提,而是基于硬质“的媒介物质性,因此,这些话语属于物质性与社会性的交织,如媒介基础设施的技术规范、法律法规。此外,也有学者主张使用“技术实践”替代“物质形态”作为分析维度,从而穷实话语建构与物质性实践之间的逻辑联系“。有鉴于此,基于数据实践在数据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位置,数据殖民主义与基础设施研究在中观层面的隐合理应考虑“人-基础设施-数据”,本文在“物质形态”与“话语建构”维度的基础上增加“技术-数据实践”维度,而非将强调实践的技术-数据实践“维度替代物质形态“维度。“技术-数据实践”作为分析维度的确更能体现人、基建与数据的互动,但与其将“技术-数据实践”直接替代物质形态,毋宁把“技术-数据实践”作为原有分析维度的扩展,因为,如果说“技术-数据实践”体现动态的媒介基础设施,物质形态显然代表着静态的媒介基础设施,后者的各类技术参数形塑前者,而前者所涉及的多元互动则推动后者的变化,这其实是一种互为表里的辩证关联。所以,后文将讨论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分析维度如何与数据殖民主义在中观层面形成互补。
图片
数字殖民主义与媒介基础设施在中观层面的分析维度展示图
上述三种分析维度贯穿数据殖民主义的三大核心内容(数据掠夺、数据关系、数据导向逻辑)。就“物质形态”而言,媒介基础设施的物质形态构成数据化(Datafication)的基础,也正是数据殖民主义的起点。数据掠夺并非凭空而来,
媒介基础设施本身的各种参数形塑着具体语境下的数据掠夺与数据关系。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随着光纤技术发展,海底电缆的技术参数发生较大改变,铜芯电缆彻底转为光纤电缆,二者传输速度差距甚大;原来基于铜芯的海底电缆在数据传输速度上与人造卫星相差无几,但基于光纤的海底电缆在数据传输的速度与容匮上皆远强于人造卫星,而鉴于海底电缆支撑着99%的全球数据传递,上述技术参数的变化自然影响着数据掠夺的规模与范围。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形成历史同样隐藏着数据资源的不平等现象。例如,IP网关虽然不像海底电缆那么形象具体,但它同样作为媒介基础设施支撑着全球数据传递,目前IP网关的历史遗留问题已带来颇为严重的地域数据流动差异问题,因为,由IP网关地址的形成历史可知,其分配逻辑类似按需分配,西方国家率先拥有了大匮IP地址,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面临着IP地址数匮匮乏的问题,这显然会导致全球数据资源的流动差异。与之相对,数据殖民主义也为物质形态”分析维度带来新视野。殖民主义视角的引入可丰富该分析维度在媒介基础设施历史层面的讨论,让研究者进一步意识到媒介基础设施物质形态的形成过程并非客观的自然发生史,相反,这很可能隐藏着外置的殖民主义思想的传承过程。
媒介基础设施研究常常关注人如何与媒介基础设施形成互动,这其实已内藏着丰富多样的数据实践,如数据收集、数据传递与数据分析。随着数据殖民主义视角的引入,“技术-数据实践”将关注人、媒介基础设施、数据三者的多元互动。在人与媒介基础设施的互动过程里,抽象的数据关系、数据掠夺与数据逻辑投射到具体的技术实践之上,所以,要弄清楚生命的数据化过程必然需要研究者关注这些技术实践上所铭刻的物质痕迹。对此,不妨以“刷抖音”为例。在此“技术-数据实践”里,人不仅与内容形成互动,也与作为平台类媒介基础设施的抖音形成互动。我们使用抖音观看基于算法推荐的各种内容时,大匮数据在此过程里不断生成、传递、分析,这些数据的运动铭刻在我们的观看实践之中;在此实践过程里,我们与内容生产者的关系日益从前数据时代的复杂多样简化为单一导向,如“流匮为王”数据为先”等纯粹的数据关系,主体间性似乎彻底转化为由机器主导的客体间性。在此情景里,主体的思考逻辑在此时仿佛与媒介基础设施的数据导向逻辑毫无区别。与此同时,数据殖民主义的引入拓宽技术实践维度的视野,从传统基础设施研究的劳工一资本主义”层面讨论延伸到人与媒介基础设施互动中的数据殖民主义批判,如社会关系的数据化倾向、个体数据的掠夺现象,这点显然有助于细化人与媒介基础设施互动的相关分析。
“话语建构”分析维度主要关注基于媒介基础设施物质形态的话语建构,这主要指各类与媒介基础设施相关的技术协议、宣传话语与法律法规等。例如,广受热议的5G事件就涉及到通讯基站的技术话语建构。在数据殖民主义语境里,话语建构将进一步关注“数据一媒介基础设施”相关话语在社会的生产、流动与实践,因为,参照相关文献,上述各环节构成了对数据殖民主义的遮蔽。在理论层面上,这种遮蔽应有两种形态:合法化与去名化。“合法化”主要关注资本如何通过话语建构使媒介基础设施与数据层面的不平等获得合理性,从而使基于媒介基础设施的数据掠夺显得理所当然。例如,在数字时代,媒体、业界、商业资本都热衷于将数据比喻为石油,仿佛数据与石油一样都属于自然资源可供任何人开采。商业资本利用媒介基础设施大肆掠夺个人数据时,常常以此为借口美化其恶行”为自然资源开采,从而获得合法性。与此类似,“去名化”主要关注相关话语而选择性忽略数据与媒介基础设施。例如,尽管数据被宣传为自然资源,但实际上,只有èé媒介基础设施的资本或政府方可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传递与分析,而相关话语往往选择性忽略或淡化媒介基础设施在此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媒介基础设施拥有权的差异。脸书、谷歌等数字巨头目前不仅本身扮演着特殊的媒介基础设施,也大量购买或建设媒介基础设施,如海底电缆、数据中心。由此观之,去名化与合法化可呈现出数据-媒介基础设施”话语建构对于数据殖民主义的遮蔽。当然,在数据殖民主义的经验案例分析里,二者仍需要结合研究对象作出一定调整。另一方面,在传统媒介基础设施研究里,“话语建构”维度主要关注“不可见”的基础设施背后的资本主义,而随着数据殖民主义的引入,该分析维度需要同时关注媒介基础设施与数据背后的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这样可以丰富该分析维度的视域。
上一篇:上帝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