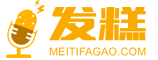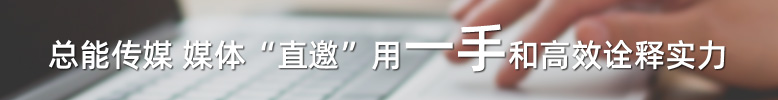陈书灵:写作自有万钧力
来源:时间:2022-09-13热度:0次
陈书灵,毕业于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2022年考入复旦大学。长到十八岁,文学始终相伴灵魂左右。于书最喜陀翁、张爱玲,在阅读中咂尝世界的欢喜和缺憾。于文看重表达的真实,试图在写作中咀嚼个体的记忆和思考。作品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
写作自有万钧力
文/陈书灵
有人戏说,我与文字的缘分写在名字里。
的确,我认字很早,上小学之前,每晚靠在母亲后背上,用小手指着,已经能说出沿途所有店面的名头,后来我想大概也正因如此,文字在我的脑海里“熨贴着大地”,和市井烟火息息相关。
我记得我刚坐到小学里时,就在朗诵比赛的现场昂首挺胸地朗声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我自己写的小故事。”现在看来那篇短短的童话已经太过幼稚,然而,不可否认,在当时那个年纪来说,在大家泥足于拼写时,我便知道只有文字能真正承载意义,实在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有些书我读得很早,先前蜷缩在县图书馆灰尘弥漫的成人阅览室虚度的下午,《穆斯林的葬礼》之宏大与清洁、看《丰乳肥臀》时游离在荒谬和真实之间的错愕以及《撒哈拉的故事》所引起的关于远方的所有想象至今都尚未褪色,反而偶尔想起渐渐能咀嚼到那时尚未理解的悲哀。
初中的时候,我爱金庸笔下的侠之大者胜过爱古龙笔下飘逸风流的楚留香。
而我读张爱玲的传记在高中读张爱玲之先,真正如痴如醉地读完两本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团圆》,才发觉爱玲不在别处,真正的爱玲只有活在她的文字里,一个“苍凉的手势”。后来又找来《十八春》和《秧歌》看,那个时期我大概写作也略略沾上这笔调,拿小说给老师看,老师笑说“张爱玲风格”,我便乐了。实则我仿得爱玲的遣词造句,又哪里能用我未经世事的少年心性故作她眼神中的冷峻和苍凉。
至于陀翁,他笔下人物面临的道德困境更甚,对人性的探讨也更为深刻。我曾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人性的多棱镜”,其他作品大类如此。
爱玲也好,陀翁也罢,二者笔下的人物哪怕只寥寥数行,背后折射的却也都是整个社会体系的沉重和无奈。曾经我容忍自己的词不达意,满足于无拘无束的私人叙事,迫不及待地拿着新作给人看时,往往要用更长的篇幅来现场向人阐释某人物的动因。可是,后来我发现写作并不是去当一只发声频率失常在深海里匍匐潜望的鲸鱼,一生无望地期待共鸣。它更近似于沟通,把一个故事讲清楚了,读者自然会在生活中不断比照,故事也就愈近于现实。
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所以在毕业将至收到素不相识的学弟来信说他读了我所有发表在校刊上的文章并深有触动的时候我也同样心怀感激、热泪盈眶。《中国校园文学》让我的文章能够被更多人看到,期间收到许多肯定,亦让我深信我的文章能够发挥沟通的价值和意义,表达欲更加蠢蠢欲动。
如果世界上没有了语言,我感谢还有文字。可若世界上没有了阅读,写作也许就会因为过于私人,而失去它的使命与生命。
不断阅读,不断观察,不断写作,写给别人看,这件事本身自有万钧之力。
在生活片片凋落以前
文/陈书灵
去医院的路上,艾萍在花店挑了一束灿烂的郁金香。四岁的儿子小巢看到这可爱的金黄色很开心,抓着她的手也是热乎乎、汗涔涔的。她还有个十五岁的女儿小杉,和许太太最好,听到许太太生病,在房间里哭了一晚。小杉有一只木盒子,盛着许太太平时送她的各式小玩意儿,已经积了小半盒。艾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瞒了女儿,不愿让她来。
许太太虽然在病中,明显地瘦下去了,但还是像画,只不过是未完成的线稿,整个人是没有颜色的。病房里淡淡的香水气息把消毒水的味道盖过去,艾萍辨识出大概是苦橘调,隐约地有些香皂的气息,一切都像是被浆洗过,湿漉漉的那种干净。可是床头的玫瑰已经有半数蔫了,许太太总是不欣赏玫瑰,大概也不花心思。当艾萍把它们换成带来的郁金香时,她像个孩子一样笑了,开始跟她说她的新裙子,也是郁金香的颜色。
艾萍听得不专心。艾萍的丈夫远远地在旁边坐着,把小巢放在膝盖上,说些无关紧要的话。有些褪色的西裤上生起了狰狞的褶子,大概毛线袜也是他破了洞的棕褐色那双,她又在庆幸他坐得远。许太太的猫跳到艾萍身上,她才回过神,那猫是灰白的,一点也不怕人,碧蓝的眼睛扬起来看艾萍。
许太太好像已经没有力气说很多话了,只兴奋了那一会儿就露出疲惫的神色。后来,许先生悄悄跟艾萍说,她治不了了,艾萍一直不信。艾萍替许太太把胳膊掖进棉被里,看到她腕子上的玉镯一直落到了小臂上。曾经她多羡慕这双弹琴的手,如今剩得只有骨节。她的手也冰凉。艾萍的眼睛忽然就红了,心里塞进一团沉沉的泡着水的棉花。许太太想向她笑那么一下,大约牵动了手术的伤口,又紧紧地咬着没有颜色的下唇。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悲伤也许是太难理解的情绪。要回去的时候,小巢睡着了,艾萍只好把他抱在怀里,用带些哽咽的声音轻轻哄了一会儿尚睡不安稳的他,已经有些沙哑的声音仍是温柔的,许太太也闭上了眼。他们和许太太告别,承诺过几天把小杉带来。
丈夫不说话,走在艾萍前面。他穿着和十多年前一样陈旧的驼色毛呢大衣,人还是和十多年前一样瘦削。他个头高,看不出年龄的漠然的背影,拖着长影,把艾萍和艾萍抱着的小巢裹在里面。艾萍试图想他此刻该是怎样的一副表情,却只看到一张模糊的面目,连五官都没有。他的背驼了点,可是这不妨碍此时此刻他仍是一棵树,随便哪一棵和艾萍没有产生过一点联系的树,褐色的树干,稀疏的枝。
她想起他们的第一次约会。他们要去看电影,电影票是想撮合他俩的朋友的单位发的。艾萍挑了衣柜里最活泼的橘黄色裙子。走近电影院时,她远远地便看到树一样的、棕褐色的、木然地站在那里的他。
电影没有内容。走回去的时候,艾萍第一次注意到电影院前那条短短的街道似乎隔几步就是一个首饰店,衬着红绒精心摆着的金镯子、银坠子又都俗不可耐。他不说话,艾萍默默地数着他们的步子。他走路快,不得不走几步便等她一会儿,艾萍红着脸快步赶上去。他们又走,艾萍总会被他落在后面。
后来艾萍说她忘记拿雨伞,于是他们又这样走回去,从电影院一无所获地走出来,她看到他正在出神地凝望她,那眼神也是平静的,令人害怕的平静,她还看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虔诚。她只好尴尬地向他笑。他抿了抿干涩的唇,低下了头。谁也没有说话。
沉默,令人发狂的沉默。
可是,再后来,有一次他们出门,他突然抓住艾萍的手,艾萍没逃。有一次,艾萍在站台踮起脚尖吻了他,看到了他眼神里惊异的神色。她大概很得意,飞快地,逃上了刚好到来的车。
那条短短的路,不过几百步,走几遭,艾萍就成了他的新娘。那种曾经让她着迷的沉默,从今以后渗注到了她人生的每一个角落,几乎让人溺亡的沉默。
他去取车,艾萍就抱着小巢继续往前走。初秋的街道还不怎么萧条,叶倒是落了一地。凋谢的花被行人踏过去,盖着车轮的印子,像巴掌留在脸上的印记,难看又凄惨。艾萍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她原以为,自己对许太太那种咬啮的嫉妒感会因她的凋落产生罪恶的侥幸感,可丝毫没有逃离的感觉,空荡的悲凉占据了她的整个思绪。像在走向结局一般走着,人生的结局,那个注定了的无力。
小巢睡得很熟,脸颊泛着潮湿的红色,密密匝匝的睫毛掩着平日里亮晶晶的眼睛。艾萍无论什么时候都觉得他睡得很好看,从他小时候就是这样。小巢晚上睡在她和丈夫之间,很安静,轻轻地呼吸。等她哄完小巢,丈夫才会进来,隔着一个小巢,他们那么倦倦地看一眼,灯就熄掉了。
大概只在早上,她才有机会在一切都还无意识的时候端详这两张脸。一张是她的创造,一张或许她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
她知道丈夫明明睡前还是干净的下巴早上又会长出胡楂,她知道他颈后有一块小的胎记,形状像荷叶,小杉有一块几乎一模一样的,她常想:基因何至于强大至此?艾萍只是坐在床边,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不再好奇这双眼睛里她的样子。她诘问自己:你爱他,抑或只是和他一起生活?可是她心里只有回响,从来不曾有过回答。
她不知道到底走了多久,只是漫无目的地沿着单行道走下去,小巢不醒,时间在机械地重复中,除了加剧腕部托着小巢的酸痛,根本不再有意义。她只是走,彻底把仍未出现的丈夫忘掉了。手机耗尽最后一格电,艾萍终于发觉他们失散了。可她却可耻地感到自由。
多晚了?天彻底地阴沉了下来。几只归巢的飞鸟掠过去,尖声鸣叫。面纱似的云雾包裹着缺角的月,是奇怪的半圆,界限不很分明,和发亮的云层融合在一起。一颗星也没有,寂寞而无聊的夜空。艾萍的呼吸变重,抱着小巢就是这样,一旦有停下来的想法,累和疲倦就同时向她扑过来,吞食她,瓦解她。
有些时候她宁愿小巢睡着,可他把沉重的脑袋靠在她肩膀上的时候,小手环着她脖子的重量让她感到无限恐惧。那是一种下坠的力量,兼着难受的窒息感,把她往下拽,她仿佛成了一具没人寻找的无名尸首,和繁茂的藻、濡湿的苔长在一起。
艾萍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抱着小巢艰难地坐下来的时候,她在车窗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不可自抑地注视那张陌生的脸,如同审视一份复杂的文稿。那里除了憔悴,令人费解的憔悴,写不下别的情绪。在苍白的面孔里,她看到一张许太太的脸。可她们毫不相像,许太太是华美的瓷器,艾萍来自悲哀,粗糙而赤裸。
怀着小巢的时候,许太太曾邀请他们一家去许先生送给她的别墅。艾萍后来曾不止一次跟她丈夫说起那层阁楼,紧闭着透明的窗,尖顶,如同锁着奢侈品的展示柜。
时至今日她仍然不断想起一整面墙上,许先生的展示柜上放在最角落的瓷瓶。曾破碎过,不知被哪个孬匠修复得很拙劣,几处甚至是欲盖弥彰,大咧咧地把伤痕摆在那里。但这不妨碍它是美的,在素净的釉色中,缠枝纹盘旋。她找不到那些奇怪的元素纹样究竟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蔓延下去。可艾萍坚信它是一种美,比起破碎,以一种更圆满的状态承受着残缺的事实,可它又是如此悲伤。
许太太恨一切不完美。她有很多时间让自己看起来完美,实际上,她也确实那样。她向客人吟吟地笑。客人哄她去弹琴,她谦让几句,坐到长凳上。后来他们又聊到艾萍,艾萍很不愿在这时被提到。她不知所措地盯着许太太雪白的腕,腕上盈透的一只玉镯在高高的水晶灯下更清澈了。她在落地镜上看到自己额前糟糕的碎发,脸色蜡黄,她不化妆。许太太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看着她,隐约地有些为她惋惜的意思。艾萍无地自容。
艾萍不得不逃,以透气为借口走向阳台,丈夫也陪着她。他们在别人的阳台以奇怪的方式面对面坐着,头顶上许太太晾晒着的各式衣物如同染坊一般丰富,精美的胸罩像一面旗子那样飘荡。
艾萍说了很奇怪的话,“我在想,等到我们死去,除了我们的愤怒,小杉,还有未来的小巢,他们能继承一些什么呢?”
丈夫离她近了一些,没有回答。他点着一支烟,只是点着,颀长的指节间灰白的烟雾慢腾腾地一圈圈绕上去,消失在那个又大又圆的月盘里。
风把艾萍的头发吹乱,发丝轻轻地挠着面颊。她的眼睛也是干涩的,瞪大了,双手环着已经很沉重的肚子,看不到自己很费力气才穿上的靴子。所有能感受到的只是那个被提前命名成小巢的胚胎不安地活动着,他的心跳如同闷闷的鼓响,砸在艾萍的心里。他又似乎是恐惧而犹豫的,为着某种注定了的命运而踌躇。艾萍感觉不到惊喜,她只觉得历史在她身上重演,也是小杉命运的重映。孩子从她的产道滑出来,生活也尖叫着从她身上褪下来,它们都啼哭起来。
艾萍注视着小巢的眉眼,问他:“小巢,你是否知道,哪里是你的家?”
艾萍把头轻轻地抵在车窗上,妄图得到片刻的休憩。呼出的氤氲的水汽黏糊在车窗上,晕染开高楼、大树和霓虹。一个女学生抱着深蓝的、看起来很沉重的书包坐在她身边的位子上,从凌乱的夹层中翻找出音乐播放器,花了很长时间捋顺耳机,并哼起艾萍并不熟悉的歌。
看起来和小杉一般年纪,她想。如今的小杉和她是疏离的,可她曾经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着手构造小杉的未来这件事上找到了快感。然而,她有时也庆幸女儿小杉不像她,更加不像她丈夫,她是一种奇怪的张扬的美。
艾萍时常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小杉放学后,骑着她的单车,穿过他们的巷子,风让她的五官生动起来。她喜欢把马尾扎得很高,于是头发在那里摇晃着。车铃不停地“丁零——丁零——”响。可是很明显,他们并没有这样一条巷子,他们只有一扇门、几扇窗。
有一次,她们出门。小杉跨在她的摩托车后座上,用手环住她,在因车速而愈加猛烈的风里紧贴着她。她甚至能察觉到她柔软的发育中的胸部,她跟着许太太学弹钢琴,可是弹得不好。许太太很会收买她,小杉对她说,像许太太那样就很好,一连说了好多她们的事。譬如许太太带她吃甜点,精致的小勺子和草莓丝绒蛋糕。小杉无比向往地把那座大房子说给艾萍听,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平常和艾萍并没那么多话。艾萍听得累了,也是恍惚,在信号灯前才猛地停车,小杉的言语写下一个突然的句点。她后来也没再说过许太太。
她的小杉不再属于她,准确地说,一直以来就是她属于小杉。从小杉出生起,她在小杉面前就没有了名字,她是“妈妈”,是“小杉的妈妈”,她因为小杉的行为得到赞美,她强迫自己笑着搂住那具曾血脉相连的躯体。“艾萍”在她的生活里缺失了,这个名字背叛了她而逃出她的生活。她不是伟大的,她卑鄙,她为不能为小杉的一点进步而欢欣鼓舞而把自己放在心里审判,狠狠地鞭挞自己。最后,心里的“艾萍”顺从得如同一只狗,对作为“小杉的妈妈”甘之如饴,忠诚地守卫着作为“小杉的妈妈”的身份。
吸引她的不是创造,而是背离。她对一种背叛求之不得,她守着自己破碎的生活,看到小杉渐行渐远,又欣慰地笑了起来。这条已经可以看得见尽头的路,见底的深渊,她将小杉推开,又为无法预知的结局感到疼痛。
那个女学生仍旧旁若无人地唱着她的歌。
小巢醒来了。艾萍略带歉意地用冰凉的指尖钩住他温热的小手,他在艾萍脸颊上亲了一下,快乐地笑起来,露出一排小小的、整齐的牙齿。他也开始唱歌,先是记得住的有歌词的,后来就只是乱哼。
小杉曾生动地跟她描述一颗恒星的生命:“大质量恒星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千万年……它们坍缩着……最终无限小,却无限沉重。”
多么漫长的时间啊。他们一级一级地走在昏暗的楼梯间,所有的门都关着,每一扇门前都摆着高高的鞋架,小孩子脏兮兮的小鞋子、阴沉的皮鞋,过于旧的高跟鞋委屈地被挤到角落,生了一层灰白的尘而黯淡下去。一切太过沉默,小巢也不再唱了,他们的脚步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听起来很重。
小巢很努力地踮起脚去摁门铃,艾萍笑着去摸包里的手机给他拍照,中途改了主意,用同一只手摸了摸小巢的发顶。小杉给他们开门,末了又把她那扇小小的房间门关起来,丈夫以那种虔诚的眼神盯着电视机里枯燥无味的政治新闻。
艾萍在洗手间脱下衣服,高高的墙让她安心,她把淋浴头打开——试着开心地笑了起来。
评论
失语者或以母之名
文/陈曦
我听不到艾萍的声音。
冷静的笔触,俗常的生活,被勾连起的时空与人际……一篇篇幅不长的小说,在节制的行文间精心营设了一个直逼现实的困顿情境。就像世界上绝大多数女性一样,主人公艾萍并未遇到生离死别的威逼,她有着平淡“和美”的家庭生活、木讷却稳当的丈夫、一双聪明可爱的儿女,她在循规蹈矩中沉浮于生活的海,犹如一枚飘荡着的无名落叶。
作为小说的“当然主人公”,艾萍把她生活的几个横截面如此“坦率”地展露在我们面前,我们“窥得”了作为妻子、母亲,作为友人乃至社会参与者的艾萍生活的方方面面,唯独——听不到她的声音。无论是作者的写作自觉还是天分与巧合的悄然同构,不得不说的是,这种充满了意蕴留白式的表达让人激动。越是无声,便越是声嘶力竭;越是沉默,便越是引人深思。
是什么消弭了艾萍的声音?又是什么让她的“失声”如此振聋发聩?
故事开篇,艾萍便领着四岁的儿子小巢去看望病入膏肓的许太太。许太太形容枯槁却依旧美丽优雅,那个曾经及至现在也让艾萍羡慕嫉妒的女性,正在她的面前展示着生命注定的凋零。灿烂的郁金香与半蔫的玫瑰在对比与象征的修辞空间给了这场会面以压抑的基调。可以说,许太太的病就是飘入艾萍生活中的那片“沉重的羽毛”,她几乎就要看清了命运的轨迹,却又被压抑得无所适从。那团塞在她心里的“沉沉的泡着水的棉花”不断膨胀,当许太太想要冲她微笑却又因伤口之痛紧紧咬住下唇的那一刻,压抑被推演到了极致,我以为,她要呐喊,我以为她要落荒而逃,而作者却在此处搁笔,把这个“直面”的片刻生生留给我们,让我们注意到艾萍的无声,注意到她想要逃离的身影。
小杉同样是文中举足轻重的一位“主人公”。作为艾萍的女儿,成长把她渐渐推离这个血脉相连的母亲,作者把她的一切都借助艾萍的思绪讲述出来。一个没有多少天分却着实聪明的、张扬着青春气息的女孩,与父母性格完全不同的她令艾萍感到欣慰,甚至兴奋。在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小杉是勇敢而乐观的,生活对于她来说是一场尚未看到终点的旅程。也恰是这一点令艾萍兴奋,那是一个与她全然不同的女孩,既可以看作是她的曾经,又可以看到完全不属于她的未来,那种有血肉有悲欢的充满挑战与阳光的未来。“吸引她的不是创造,而是背离”,可以说这种对背离“慈悲”的向往,便是艾萍渴望逃离生活最为幽微又最为恰切的注脚。
小巢是沉重的。从一个胚胎开始,他便是坠在艾萍身体与精神上的沉重的负载。小说中对艾萍孕育生产小巢时的心理描写实在精彩,她的不安踯躅,她的恐惧与叹息,沉甸甸地坠压在读者心中。“哪里是你的家?”艾萍对一个生命刚刚缘起的婴儿问出这句话时,那种对命运、人生、来处与归宿的惶惑在这时达到了顶峰。
小杉、小巢,复刻、脱轨。艾萍失去的声音似乎被找回来了,但全篇文章,除了两句沉重的询问,再无她的言语。那被找回来的声音,全然被名曰“身份”的世俗之手摁压进生活的喧嚣之中。艾萍与艾萍们除了彷徨于无地,又有何法?母亲、妻子、女人,一个比一个沉重的身份,借助日常的驳杂,一点点抽离了主人公的声音。作者毫不留情地让我们目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艾萍,成为一名失语者。小说自此具备了超越作者年龄层的深刻。
当然,我们绝不会忽略艾萍的丈夫,一个从恋爱时期便沉默到令人窒息的男人,老旧的衣衫,寡言的性格,无趣的生活方式,他比艾萍还要缄默,又这样缄默地完成了艾萍身份的所有对位:父亲、丈夫、男人。作者借助这个形象,为读者洞开了一个崭新的理解维度——霓虹闪烁的城市,飞速发展的时代,又是什么塑造了他的沉默?他又是谁?谁让他们的性格逐渐如出一辙?
实际上,声音便是表达,在小说中更是与腔调共同构建出人物性格的重要乃至唯一途径。不同人物的性格又是小说表意行之有效的聚焦点,这些焦点至关重要,如托尔斯泰所言:“艺术的事就在于找出焦点并把它显示出来。”(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漓江出版社,1982年,第76页)但有时,消弭性格亦是显影焦点的一种形式,留白给了人物与故事以张力,从而更具有现实指涉的强烈意味。
我想,当作者写下题目《生活片片凋落以前》的那一刻,便已经意识到,生活片片凋落以前,依旧是片片凋落的生活,只不过,我们应该活着,作为自己活着。
陈曦,天津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青年评论家,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文学评论见于《光明日报》《中国图书评论》《文艺报》《新京报书评周刊》等报刊。
上一篇:写一篇新闻稿就是生一个孩子
下一篇:不得不看的央视神仙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