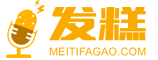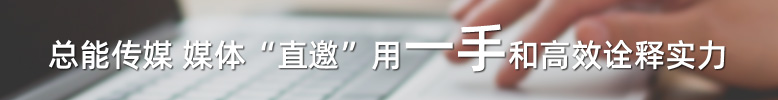十年战地记者告诉你如何分辨俄乌战争新闻真假?
来源:时间:2022-02-28热度:0次
大家好,我是陈拙。
这两天全世界都在关注乌克兰。但有些假新闻你要是相信了,真就有点危险。
我自己都差点中招了。
之前一直有人说,不管多危险的路段,只要贴咱们国旗,就会安全通过。我还想要不发条朋友圈,让在乌克兰的读者们注意安全。这消息是真的,但局势一变就不能用了。
直到中华网军事频道出来提醒:最好分一下地区,比如乌克兰西部还不稳定,过早贴旗,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都是希望同胞安全,请大家多关注大使馆那边的消息。
乌克兰大使馆的通告
不单说这个,48小时了,我所见几篇传播量几十万的媒体消息里,也掺杂着一些假信息。甚至有些是故意而为之,就为了博取巨大的流量。
为什么普通人此时特容易成为舆论场上被割的韭菜?
我想,或许是因为这两点:
第一, 我们生在中国,距离战争太远了,更不会了解一旦发生战争,信息是如何传递的。
第二, 现代战争的特点就是“引导舆论”,许多人为的假信息,往往背后藏着战争操盘手的目的。而我们掌握信息分辨的方法却是不足的。
我为此请教了战地女记者梁玉珍,她曾在中东战场呆了10年,只要起冲突,国内第一个能看的就是她的电视报道。
她曾在天才讲过自己的故事,但今天可以再说一遍,详细告诉大家,那些真实的战地信息,是如何被她们传递给你的。中间又付出了多少代价。
而在结尾,她也会教大家一些信息分辨的方法,帮你提高信息素养,像她一样临战不乱。
1999年,国内在中东没有一家媒体能够进行电视直播。当时的中国人,无法快速看到那个大陆发生了什么,哪怕有天大的事,也只能等待第二天报纸。
梁玉珍当了20年记者,她没想到自己将会是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她从大学那天就开始学习阿拉伯语,直到46岁,她接到命令——
飞往中东,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个记者站。
台长的要求是,这个记者站得覆盖西亚和整个非洲,涵盖70多个国家。其重点地区是中东;台里能给她的人员是,一个搭档,只有她们俩。
到了当地,她却连总统府等重要地方的采访都不被允许。
总统府开发布会,有同行扬起手上的记者证对着梁玉珍晃了晃,“有了这个才能去”。
她眼睁睁看着别的记者坐上了接驾的汽车。
她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都要尽快办成这件事儿。
她跑到了当地的新闻中心,经人推荐,又在总统府新闻中心找到了负责的塔利克将军。
梁玉珍在将军面前说:“我会做到开罗最火,中国的第一媒体。”
将军告诉她,总统府记者证可以给,能不能把握住,就看她能不能实现这个承诺了。
她说可以,但记者证不能一张,要两张。
因为电视新闻,必须要两个人搭档。她自己既是出镜记者也是编导,兼顾不了摄像。
她最终从将军那拿到了两张采访证。
后来又有人在梁玉珍面前显摆这个证件,她默默掏出来2张采访证,说不就是这个吗?
豪言壮语说出去了,和将军的赌约却还没有完成,一年之内如果无法做到最火,这些证一定续不上,那中国央视想要在当地建站的计划也就泡汤了。
梁玉珍只有一个解决方法:不休息。
建站的要求是稳定每日刊发消息。下来的几个月,梁玉珍一直在各地跟踪报道巴以地区的冲突事件,报道完一个,紧接着就要赶往下一个现场。
就连和朋友一起吃个海鲜,都能接到线报附近有枪击案,她都要马上赶过去,没有任何防护,报道眼前的两队人马激烈火拼。
采访完,她就蹲在地上写稿子;写完,就站在那里录制解说词。
这些事她都是在交火现场完成的。
梁玉珍一直觉得,离子弹越近,电视机前的中国人们就能了解情况越详细。
那些日子里,她不休息,她追着危险跑。最终不仅满足了建站需求,还兑现了和将军的承诺。
她本来是要报道阿拉法特刚被空袭完的废墟,特意站在了离坦克50米的位置。
镜头里,本指向阿拉法特官邸的坦克炮口,在发现梁玉珍后,缓缓调转,指向了她。
在坦克调转炮口对准梁玉珍前,她仍在镜头前直播
这个镜头,让她一战成名。
说来也巧,在其他国家的节目中,拍到了梁玉珍给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一百美元。
这组镜头在土耳其电视台9个频道反复播出,大家都记住了那个身穿红色夹克上衣,后背上印有黑色字体——CCTV。
如高频率的采访,如此危险的近距离,她的节目组成了当地第一。
她被科威特埃米尔(国王)握着手,对方说 “好几亿的观众,你真了不起。”她出席发布会,不论什么时候,总能听见:“下一位,CCTV,埃咪娜,梁”。
后来,巴以冲突一波接一波,记者站在报道的忙碌中也步入正轨。
但梁玉珍仍然不能休息。
因为美国不听联合国劝阻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直接对伊拉克开打。
“开战当天,我却没有职业的兴奋感。”
梁玉珍很希望自己在新闻报道上有突出业绩,但在战地呆了这么久,看到过无数次袭击后的惨状,她真的不希望战争发生。
她报道这些,不是为了其它,只是想竭尽所能,到最接近主战场的地方,记录战争的残酷。
所以战场上的士兵不休息,她就也不能休息。
开战前的前半夜,梁玉珍坐在那里盯着自己的两部手机,心里慌了。看着两军对峙的气氛,估计只剩几分钟了,可电话一直占线,联系不到后方的人。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她连忙接起来,”你千万别挂,马上就要开打了!”
话音刚落没多久,就听见一阵尖锐的警报,和第一轮爆炸响起。在这样的声音中,梁玉珍缓缓开口:“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开始了”。
这句伴随着爆炸声的简短消息,成为了国内首条电视媒体报道美伊战争的声音。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她紧接着赶往了机场,她要去拿央视总部速递的防弹衣和防化设备。防弹衣很重,就连抬个胳膊,肩部也会受到影响,但她始终都举着话筒。
在接下来的40多个小时里,梁玉珍没有一秒钟合眼。
她每天往返七八百公里,还要在中国时间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开始,完成对战场报道的直播。到了凌晨,仍要完成其他频道的直播任务。几乎每个小时,她都在用电话传递最新的消息。
她忙得脱不开身,最终的结果是,开罗记者站上新闻联播的次数在所有记者站中位居第一。
但梁玉珍一直说,她没能真正深入到一线主战场。
报道美伊战争的时候,她只能在边境游走。她也遇到过好几次被军队用枪指着鼻子的事情——这时候,要用一种十分窝囊的姿势:把双手缓缓举到至少与耳朵齐平,翻转手掌才能离开。
她觉得这不仅是一种耻辱,更是一种无法报道全部真相的遗憾。
比如上述的画面,就无法播放。她决定从另一个角度,从受到战争波及的百姓切入,以此展示战争的残酷。
2003年3月27日之前,她结束了在主战场的采访,但没喘口气,又奔向了难民营。
她收到消息称,有一个跨越六百公里,从伊拉克来到约旦,在难民营里生下孩子的女人。
她要去见见这位母亲。
次日,梁玉珍起了个大早,购买纸尿裤,奶粉,了解难民营的情况,拦了辆出租车直奔营地。
当天的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她撩起供婴儿居住帐篷的门帘,感受到一阵令人窒息的闷热。
在这间狭小的帐篷里,堆满了床垫、衣服等杂物。女人坐在床头,很瘦,脏兮兮的,抱着孩子双目无神地看着前方。
房间里到处都很脏,只有孩子身上很干净,被包在白色的襁褓中。
梁玉珍摸了摸,很嫩。女人不允许拍摄,但允许梁玉珍抱抱自己的孩子。
梁玉珍抱起了这个只来到世界上只有8天的孩子——这是她第一次抱起这么大的婴儿。
虽然她不知道这么大的孩子怎样才算健康,但怀中的重量让她下意识觉得不对劲,这个孩子只有3斤左右。
小孩子眼睛滴溜溜的看着梁玉珍,她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她在儿子出生时难产,见到孩子的时候,隔着玻璃窗,张着同样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望着她。
对于这个婴儿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轰炸,而是沙漠中的毒虫,还有白天接近最高能接近50摄氏度的气温,在晚上可以骤降到个位数。
她只觉得自己心里堵了东西说不出来。就这样抱着孩子,满脑子都是这孩子,怎么能适应难民营里的居住生活?
她突然发觉自己帮不了什么,哪怕把自己的物资全给这个母亲,对方也无法好好生存。
后来梁玉珍试图再去寻找这对母女的消息,杳无音讯。
无力感让她开始厌烦,不想去报道这些,不想见到战争,也不愿意和死人的事情打交道了。但她不能,因为她不做,这些真相永远不会被国内的人在电视上看到。
她想到这,更不让自己休息了。
她不断走访难民营,到空袭、导弹轰炸后的现场,用镜头记录下藏在残垣断壁中的,婴幼儿的服装。她要通过自己的报道,唤起人们的关注,争取到国际的救援。
她在报道中说,“当前这里无辜居民受战争影响,处于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急需国际救援和各界的人道主义援助。”
报道播出后,国际救援队真的赶到了。
她不眠不休的报道救了人。
她不知道的是,有时再努力,也救不了同胞和自己。
踏进灵堂的一瞬间,梁玉珍就发火了。
三个中国军人的遗体,躺在布置一片狼藉的灵堂里,他们穿着军装,脸上布满一道道血迹,身体一侧还缠绕着渗血的纱布。
她斥责在现场的人,“真是太不像样了。”
那是一次连环恐怖袭击,中国军事交流团传来消息,四名大校遇难,有三位把生命永远留在了约旦,只能把遗体送回国内。梁玉珍说,如果没有这次袭击,这三人回国是要提干的。
国家一下损失了三个未来的军级干部。
梁玉珍凑近遗体看着,他们仍然瞪圆了眼睛,张着嘴,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
她要来热毛巾,盖上了遗体的脸,暖了暖。她让翻译告诉工作人员,要慢慢按摩着死者的面部,过了一会儿,她用手轻轻合上了他们的眼睛和嘴巴,盖上了国旗和军旗。
她说,“至少不能让同胞死不瞑目。”
梁玉珍望着遗体瞪大的双眼,足足5秒钟,她很想知道在遇害前,脑子里到底会想什么,才会这样睁着眼睛死去。“是在想他的家人孩子吗?还是在想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一次报道反战游行时,她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游行活动里都是人高马大的男性,她在人群里还没多久,就发现前方有警察拿着棍棒走了过来。人群开始骚动,发了疯似地向后跑了起来。
50岁的她,在一群小伙子面前像一张纸,挣扎中她失去了重心。
她这才知道,人在临死前,是不会想太多的。
她当时只想抓住一个周围人的裤腿,想要站起来。可那还有那么大力气,思维渐渐开始停滞了,她张着手,却什么也抓不到。
她把自己装满设备的双肩包抱在怀里,使劲把头埋在胸口和包的中间。“我可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感觉自己当时快不行了,就只护住自己的脸。受伤的话,镜头里会不好看。”
她也知道自己不像军官那样,有着辨识度极高的服装(印着CCTV的台服不是每一次都穿)。在这个遍地都是穿着防弹衣的地方,如果死了,只有护住脸,才能被国家认领回去。
踩踏中,她失去了意识。
最终的结果是,她被踩成了重伤,医生建议好好休息。
可梁玉珍养伤了2天,就又出现在了镜头里。
因为她没有办法休息,“记者站就两人,少一个很多事都办不成。”
期间家人也给台里打电话询问,中东就俩记者,为什么只有她不见了。
她不想让家里人担心,和儿子通电话后,她选择再次出镜,隐瞒家人自己的真实情况:血胸、脑震荡。
镜头里不会拍到她受伤的下半身。
没多久,2006年,黎巴嫩和以色列开始了新一轮交战。
她带着一身伤病走向了战地。
梁玉珍遭到踩踏的反战抗议游行
这次采访,梁玉珍签署了一份生死状:以色列军方对记者的死活不负任何责任。
她亲眼目击了以色列向黎巴嫩境内发射炮击。并排的重武器,在一瞬间接连发出炮弹。
她的耳朵嗡嗡作响,只感觉一阵尖锐的头痛。脚下的土地开始震动,感觉自己快要摔倒了。她再次感受到了无力感,这次,是对战争的无力。
身为一名记者,在军事行动面前,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但仍有能做到的事情——
她要靠地再近一点,用最清晰的镜头,最直接的画面,最真实的声音,还原现场,引起对战争的憎恶。
2006年,梁玉珍在以色列边境炮击黎巴嫩南部的炮兵阵地
她来到核心战场的上午,就遭到火箭弹袭击。
起初,只是刺耳的警报声喋喋不休,紧接着,火箭弹落在了不远处。
梁玉珍叫上搭档,逆着避难的人群冲了过去。她顾不上躲避,循着声音的方向寻找落弹点。
她经历了太多次,甚至根据爆炸的声音和震动,都可以判断炸弹有多少吨。爆炸声越来越近,就在前面不过百米,她发现了一个篮球场般的深坑,烟尘还没有散去。
就在这个场景里,伴随着持续的爆炸,她做了现场报道。
安静下来后,她一阵后怕。如果她不是一名记者,她绝对不会选择来到这个地方。可生活在这里的人,却没有选择的余地。
哪怕搬离这个国家,只要不离开中东,谁也说不好明天谁和谁又打起来了。
自从战争打响,她一直都说时间不够用,连轴转几天,一个还没报道完,新的爆炸就发生。
2006年8月9日,黎以战争陷入疯狂交火,她终于撑不住了。
过度劳累先是让她开始发烧,被踩踏的旧伤也让她落下了病根,经常扭伤。
她开始失去力气,走路都连续摔倒。
她在日记里写道:“双腿膝关节和左脚早已肿的无法走路,浑身酸痛难忍,翻个身都很困难,夜里开始发高烧,特别想起来倒水喝,挣扎了半天无果,又摔到了地下,就这样瘫在地上,直到早上被饭店服务生发现。”
“医生不肯出诊,我真的坚持不住了,急需救援。”
常在河边走,梁玉珍终究没有躲过战争带来的病痛。
她病倒一周后,陷入了昏迷,醒来时已经回到北京。休养了两个月,又接到任务,2006年10月底,她带病带伤返回中东。
两年后,又出了车祸,这下她再也站不起来了。
梁玉珍开始了复健,她把医生给列的治疗方案一个一个试,就用自己身体当样本,直到遇见合适的。但对于腿来说,如果做义肢的话,必须要和皮肤紧密接触,而且还会大量出汗。
由于过敏体质,医生只能以不截肢为前提治疗。
她左腿因多次手术,共打了70多根钢钉。外固定架重5公斤,在佩戴固定架的2年10个月(840天)里,没有办法洗澡。最终做了关节融合手术,永远无法弯折。
以前在中东,她都保持着每日洗澡清洁的习惯。
她在床上躺了几年后,退休了。
遗憾是有的,她当初接到的命令,是建成的记者站,要覆盖西亚和非洲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最关注的22个阿拉伯国家,她已经走完了21个,至于最后的索马里,她再也没有机会去了。
但也有好消息,10年来她在中东的努力没有白费。
2011 年开始,央视建立了阿拉伯语频道,然后招了一大批记者。
两年之后,又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部署了多个记者站。
那时,叙利亚仍在内战,她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她努力复健了3年,开始写书,将最真实的战场,当年没有被镜头记录的事整理下来。
她在书中写到,做“新世纪巴勒斯坦人的希望”那篇报道时,来到了一个叫做各拉拉村的地方。刚进村子,看见有一个废弃的油桶,上面还插着长长的杆子。几个巴勒斯坦人,正围着这个杆子,往上升国旗。
搭档打开了摄影机,准备拍几个镜头。就在这时,对面的巴勒斯坦人一句话也不说,冲着搭档的脚下,直接开枪进行扫射。
她冲了上去,大喝:“我本来对巴勒斯坦人很同情的,但你们竟然这样做?”可对面只是嬉皮笑脸地说,这只是个玩笑。
她说,这些是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国人极少能经历到的。“现实的问题是,仅仅只是看到电视荧幕上对战况的报道是远远不够的,短短2、3分钟一条的新闻背后,有太多镜头无法捕捉的故事。”
记录这种真实战地的意义,或许就像书中序言里写的那样,让人们思考这个问题:站在历史新的十字路口,未来人们应该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路?
可对于她而言,一条腿没有办法弯折,坐下都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更不用说长时间写作。
一个姿势不能保持太久,只要超过半小时,就会严重肿胀。她的腿即使什么也不干,也会持续的疼痛。而使用助步器复健,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疼痛,也没别的办法。
她记得医生说,这种疼痛可能会持续10年左右,也可能一直就这样。
她没有休息,她还在写。这本书和她过去的报道一样,都是能够警醒人,能救人的记录。
历时2年,书籍出版了。
这本书也火了,在出版界和图书馆的会议中,收到了很多插签。首都图书馆也收藏了这本书。
有人评价说,往往新闻背后的故事更加精彩,她让大家看到了更加真实的中东。
与此同时,在战地工作不规律的生活方式,给她带来了另一次伤害。
2018年,梁玉珍确诊了乳腺癌。当她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是愣了一下,很快就释怀了。早年奔波,本身体质也差,加上多年的体力透支。算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这很正常。”
她配合医生,切除了一侧乳房。
她很不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责怪“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件事”,因为与其担心,不如想想以后该咋办。有次接受采访,她穿着一身儿子的阿根廷足球队队服,感觉自己看着很中性。
她说自己是一个非常注重形象的人,“但现在,能怎么遮掩怎么来吧”。
唯独有个真正的伤心事。
住院前,她在儿子家住了两天,和她特喜欢的小孙女睡在一张床上。等晚上孩子睡着了,她一想到住院后,再也没办法抱抱这孩子了,心里直堵得慌。她想起医生告诉她,癌症患者有个5年的坎。
车祸毁掉职业生涯时她不哭,这次在孙女身边,她没能绷住。
医生让她复查,她没去。“5年过去了就过去了,没过去想也没啥用。”
梁玉珍从不去计较余下的时间,她决定做些什么,当然不能只是休息。
她开始为乳腺癌患者发声——写文章,参加活动,为她们争取一些权益。
这几年里,梁玉珍一直给公益机构义务写稿、编辑稿件,每周发一次稿。她有一张粉色的写字台,原先是买给孙女用的,现在成了她的办公桌。打开电脑,坐了下来。
她给朋友展示桌子下面的横梁,每一次先坐下,然后把脚搭在横梁上,再拉动桌子调整。
可一个新起步的公众号,稿源很少,她说要是自己精神好的话,都是亲自写。“但现在啊,精力不多了,也写不了那么多。”
但打开发布文章的列表,她指着最后一栏,说:“已经发了78篇了。”
她说乳腺癌群体的人,好多生活条件比较差或者文化比较低,有问题也不知道找谁去问。所以在公众号里也经常要搜寻一些有关方面的知识。如果有人来问,都会给他们解答。
有人牵头,拉着大家抱团取暖,说不定就能多坚持治疗。
她仍然在用一个记者的方式,试图去帮助与拯救一些人。
她撩起了自己的裤腿,她的膝盖侧面有着一个越深一厘米的“倒T字形”沟壑,从大腿侧面,延长到膝盖后分岔,顺着膝盖向链接了大腿和小腿。小腿肚子有两个芒果大小的深坑。
她说,也挺遗憾的,因为离城里比较远,她一直没有办法去安抚病友。
她总是这样,不管是当战地记者,还是负伤后在家里,都时刻有新的任务期限逼着她,一刻不停地向前走。而她也知道,走得越远,自己能帮助的人就越多。
她一直在和时间赛跑,从来没有休息过。
她在那个公益组织里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我死了,反正也没什么遗憾,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墓志铭是:这里埋葬的是一个生命的奇迹。”
或许这是一个不眠不休的女人,在长眠之前最重要的心愿。
但这样一个灵魂的存在本身就是奇迹。
下一篇:贺州广电“阳光小记者”等你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