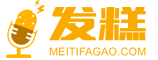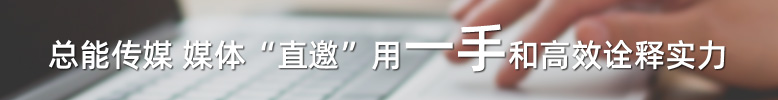一个公众号编辑来到神父前
来源:时间:2022-02-08热度:0次
礼拜二的最后一抹余晖低低掠过望京、三里屯和青年路,天光四敛的一霎,在这些挤满公众号小编、野生意见领袖和二手信息肉喇叭的地盘上,敲击键盘的声音渐渐归于平静。最迟钝的编辑都放下了手上的电子烟,任凭这样一个声音抵达心头:
“公众号,完了,公众号,完了,公众号,完了……”
于是,像被感召了一般,他们在亲手染污的信息河流上停下摆桨的手,面面相觑,诚实地舒展出应有的空洞。
午后,一个公众号编辑来到神父前,在黑魆魆的用樟木拼装而成的告解亭里掩面而泣。
“我是个青年亚文化公众号编辑,自我夸耀地说,我是个恋尸癖,因为青年亚文化死了;实事求是地说,我是个骗子,因为我述说的青年文化都是假的,所以我宁愿说它死了。”
“我们就这么夸大其词地捏造着网线另一端的故事,该死的VPN,以及它赋予我们的唬人的特权。如果真有人把那些东西当成酷 —— 天哪,就是这种可能性令我心焦!那只是用普遍意义上的酷升华过一遍,用最大公约数计算出的共情对焦过一遍,最后用通货膨胀后的修辞批量包浆的精神垃圾食品。”
“我们用尽浑身解数,不去描述事情本来的样子,而是将事情夸大到恰好可以被那些令人目眩的形容词形容。就像……就像一个纸杯蛋糕!你会发现它们的叙事是蓬松中空的,即便它们经过烘焙,膨胀到挤满了各种意义的纸杯。”
“是的,我就是流水线上为蛋糕充气的那一环,最可怕的是,”他顿了顿,“我却渐渐不再为此脸红。”
这是一个燠热的星期二的午后,神父从午睡中径直醒来。
前一天他曾聆听一位西二旗产品经理的告解,再前天则是社科博士、大厂寄生人和一个来自遥远南方的妓女,除了妓女,其他人都抱怨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场卖淫。
神父早在十五年前就已不会为任何程度的坦诚而感动,他甚至不知道面前这位忏悔者究竟是恋尸癖、骗子、还是出轨的蛋糕师。
“实际上我是个绝望的矿工”,
忏悔者又说,没察觉到神父眼中更浓的疑惑,“我挖掘着每一个事物的意义,总想激起读者心中哪怕一丁点儿获得的错觉。直到没有意义,直到意义的意义都被陈词滥调的陈词滥调磨平。那一天,我的报应来了。”
“那一天,我看到一切事物时看到的却是他们的符号,看到一切符号时看到的则是符号的隐喻 —— 但我偏偏看不到事物本身。
我描述了所有我见过或者没见过的东西,同时污染了它们。我病了,我是感官上的残障人,如果我的视野内置了解读的滤镜,那么我的眼睛就遮蔽了它本身。”
“什么时候开始的?” 神父问。
“发现失去感觉的那一刻。也许我曾经有感觉,但开了第一百次该死的选题会之后,我真的不知道了。
你能想象吗,选题会,让我打个比方,一群人围成一个圈,一个人突然撩开上衣,掐着自己身上某一点说,‘这是我的G点,你们捏捏自己这个地方觉得爽吗’,所有人依次开始掐,有的人说爽、牛逼、找得准,有的人说什么玩应没啥感觉。”
“啊,这真难以启齿,” 公众号编辑小声说,“现在,就连我们互相掐都没有感觉了。”
“我的孩子,如果真如这般痛苦,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神父问。
“在我看来,所有能坚持下来的人,本质上都是露阴癖,喜欢想象别人惊讶的表情,但又因为一无所知以及一无所有,于是只能突兀地解开裤子,用不在乎自己到底大不大的自大去刺痛别人。”
“停一停吧,”神父叹了口气,“这是一种优越感,不是吗?”
“我的孩子,”他接着建议道,“或许你应该释放囚禁在自我(ego)身上的目光,扫视一下周围,看看那些更不严肃的,或者更严肃的可亲的同行们。”
“我亲爱的神父,人人都知道,谁都能当公众号编辑,就像不论什么货色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不论什么货色的人都能找到他的读者。
当我环视周遭,发现那些不严肃的,已经开始表演起了公共色情秀,他们诉说男人被男人强暴的故事,只需用你要努力奋斗实现阶级跨越以避免这一切作结,他们诉说女人被男人强暴的故事,只需用你要精神独立成为女权大宝贝儿把这一切当做前车之鉴作结。
说到底,人们还是喜欢看强暴的故事啊”。
“而更严肃一些的呢,那就谈谈新闻理想吧。每当听见这个词,我总忍不住怀着一如既往的小人之心揣度,他们实际上指的,是自己无法抵达的文学梦。”
“他们会说,这个故事太有意义了,我有使命把它报道出来!呵!我看他们只是缺少创造的天赋,只能通过编排一番他人的人生,把叙事的欲望胡乱发泄一通。
看看那些稿子,他们把好端端的时间线打碎拆分,制造一些自以为是的蒙太奇,把毫无联系的事情生拉硬扯在一起,营造一些别有深意的互文,再穿插上某个人物微妙的动作或神情,作为他们自以为是判断的脚注和余音。呵!他们去认领这些故事,就像认领他们的新闻理想。”
“或许,你可以另择它路,比如…”神父最后挣扎说。
“难道让我去拍短视频吗?!”因为恐惧,公众号编辑抢在神父之前喊出了这个词。
两人陷入沉默。
“主啊,” 神父叹息,“这是个没有信仰的年轻人,所以才会把所有的信仰看做欲望。”
“主啊,但现在他也没有欲望,他欲望着有欲望。”
“迷途的羔羊,饥饿的旅人,”神父看向他,“你需要一次神迹。”
比如呢,比如什么神迹呢,一篇十万+,一次三十万的头条投放,或者抖音突然消失,让公众号黄金时代回眸一次,还是,还是再听别人轻轻地唤我一声,媒体老师?
那就让神迹出现吧,时光倒流,一位明显局促不安的媒体老师再次出现在觥筹交错的名利场,他摩挲着他的A类媒体证,心里酸楚地知道,他真正能和这个世界能交换的,也只有一篇通稿,而他真正能和另一位媒体老师交换的,除了一只中南海,几句流言蜚语,只剩下对彼此真诚的轻蔑。
“我的孩子,”神父早已习惯对这种无能为力心怀坦然,“据我理解,你的工作溢出了,你的思考、你的语言都成了对思考和语言本身的戏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停止自满于这个无聊的游戏,它把你的脑袋都搅浑了。”
公众号编辑没有说话,即便他没有说话,他仍害怕眼下的沉默成了对沉默的戏仿。
“我还需要更多的字吗,我还需要更多的词语吗,我还需要更多的修辞吗,当然,当然,当然!我需要投身其中才能与之斡旋,啊,我亲爱的神父,如果我有信仰,那就是这斡旋本身,我现在需要的神迹,是一些真实的劳动,和一张真实的纸钞。”
这是一个星期二的沉闷午后,神父在告解窗的后面打起了盹,没有人能真正地做一个对社会没用的人,这是他最后对那位年轻人的安慰。
像是对所有让他厌烦但却不得不施以庇佑的人一样,他的忠告是一个以安慰为名的无聊诅咒。
上一篇:录取通知书亮点太多,发稿都说不完
下一篇:新闻与写作讲座